日前,復(fù)旦大學(xué)、華東師范大學(xué)、同濟(jì)大學(xué)、上海大學(xué)、上海師范大學(xué)等上海高校學(xué)者共同發(fā)起了“今天,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文學(xué)教育”系列活動(dòng)工作坊。6月28日,由同濟(jì)大學(xué)中文系主辦的第一期工作坊“人工智能時(shí)代的文學(xué)教育與文學(xué)閱讀”在同濟(jì)大學(xué)召開,來自復(fù)旦大學(xué),華東師大、上海大學(xué)、上海師范大學(xué)、同濟(jì)大學(xué)、中國(guó)社會(huì)科學(xué)院、澎湃新聞·上海文藝等高校及相關(guān)研究機(jī)構(gòu)的30余名與會(huì)者參加工作坊,圍繞相關(guān)問題進(jìn)行深入研討。本文為上海師范大學(xué)中文系系主任、教授王宏超在首期工作坊上的主題發(fā)言稿。
2014年,八十五歲高齡的米蘭·昆德拉在“沉寂”十年之后,出版了一部中譯本只有三萬(wàn)五千多字的小說:《慶祝無意義》(La fête de l'insignifiance)。老人的作品多少總有些遺囑的影子(其實(shí)所有人又何嘗不是如此),昆德拉這部多少有些令人費(fèi)解的小說,以談?wù)撆说亩悄氶_始,最后卻在說:
無意義,我的朋友,這是生存的本質(zhì)。它到處、永遠(yuǎn)跟我們形影不離。甚至出現(xiàn)在無人可以看見它的地方:在恐怖時(shí),在血腥斗爭(zhēng)時(shí),在大苦大難時(shí)。……我的朋友,呼吸我們周圍的無意義,它是智慧的鑰匙,它是好心情的鑰匙……[米蘭·昆德拉著,馬振騁譯:《慶祝無意義》]
昆德拉并不是第一次在講“無意義”了,從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》開始,他就在說:“如果生活中的第一次彩排便是生命本身,那生活有什么價(jià)值?”他在《帷幕》中又說:
我們最大的問題之一難道不就是無意義?我們的命運(yùn)難道不正是無意義?而如果是的話,這一命運(yùn)究竟是我們的不幸還是我們的幸運(yùn)?是對(duì)我們的侮辱,還是相反,是我們的解脫,我們的逃逸,我們的田園牧歌,我們的藏身之所?[米蘭·昆德拉著,尉遲秀譯:《相遇》]
昆德拉為什么反復(fù)在強(qiáng)調(diào)“無意義”?人類難道不是如馬克斯·韋伯所言,是懸掛在自己所編織的意義之網(wǎng)的動(dòng)物嗎?昆德拉是在表達(dá)虛無主義嗎?

昆德拉在《被貶低的塞萬(wàn)提斯傳承》中,提到胡塞爾在1935年所做的幾次有關(guān)歐洲人文危機(jī)的演講,此即《歐洲科學(xué)危機(jī)和超驗(yàn)現(xiàn)象學(xué)》一書。昆德拉總結(jié)胡塞爾的說法,歐洲所面臨的危機(jī)對(duì)歐洲命運(yùn)攸關(guān),“危機(jī)的根源在現(xiàn)代(les Temps Modernes)初期就已經(jīng)出現(xiàn),在伽利略和笛卡爾的著述里,在歐洲科學(xué)單邊性的性格里。歐洲科學(xué)將世界縮減為技術(shù)與數(shù)學(xué)探索的單純客體,將具體的生活世界(也就是胡塞爾所說的die lebenswelt)排除在他們的視野之外。”人在理性世界里,處在“存在的遺忘”的狀態(tài)之中,而人的生活世界,“也沒有任何值得注意之處:人的具體存在被預(yù)先遮蔽,被預(yù)先遺忘了。”
伽利略與笛卡爾代表的是啟蒙現(xiàn)代性。笛卡爾、黑格爾等將“思考的自我”(ego pensant)理解為一切的基礎(chǔ),追求絕對(duì)真理。胡塞爾說:
從笛卡兒起,一種新的觀念支配了整個(gè)哲學(xué)運(yùn)動(dòng)的發(fā)展……首先是數(shù)學(xué)(作為幾何學(xué)和作為關(guān)于數(shù)和量值的形式化的抽象理論)被委以普遍性的任務(wù),這種任務(wù)在風(fēng)格上從原則上說是新的,是古人所不知的。[埃德蒙德·胡塞爾著,張慶熊譯:《歐洲科學(xué)危機(jī)和超驗(yàn)現(xiàn)象學(xué)》]
古希臘雖然有對(duì)經(jīng)驗(yàn)的數(shù)的理念化,有歐幾里得幾何學(xué),形成了系統(tǒng)地一體化的演繹理論,“但是歐幾里得幾何學(xué)和一般的古代的數(shù)學(xué)只知道有限的任務(wù),它們只是有限的、封閉的先天原理……古人到此就止步不前了。但是停留在這里就失去了把握無限任務(wù)的可能性。”
近代的哲學(xué)和數(shù)學(xué)在柏拉圖的基礎(chǔ)上前行,通過伽利略對(duì)自然的數(shù)學(xué)化,自然成了數(shù)學(xué)理念化的對(duì)象。
通過在時(shí)空的形狀方面觀念化物體的世界,數(shù)學(xué)創(chuàng)造出觀念的對(duì)象。數(shù)學(xué)從沒被規(guī)定的普遍的生活世界的形式中,使空間和時(shí)間及其在它們之中可想象的經(jīng)驗(yàn)上可直觀的形體成為一個(gè)真正的客觀的世界。這也就是說,數(shù)學(xué)創(chuàng)造出一個(gè)在方法論上普遍地對(duì)于每一個(gè)人來說都可清楚地規(guī)定的觀念對(duì)象的無限的總體。這樣,數(shù)學(xué)最早向我們表明,用一種先天的普遍的方法,可以使原先主觀地相對(duì)的、只是在一種模糊的一般觀念中可想象的對(duì)象的無限性成為客觀地可規(guī)定的,和真正地按其自身的規(guī)定性設(shè)想的東西,更確切地說,對(duì)于這種無限性可以事先在其一切對(duì)象及其對(duì)象的性質(zhì)和關(guān)系方面加以規(guī)定和決定。[《歐洲科學(xué)危機(jī)和超驗(yàn)現(xiàn)象學(xué)》]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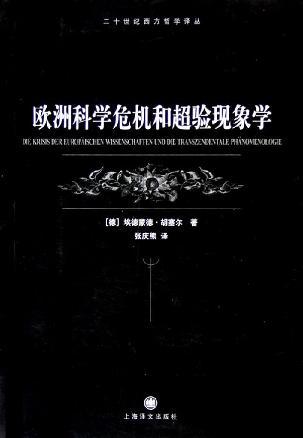
生命充滿著偶然,我們卻用必然性來解釋事件。必然性令人踏實(shí),人接受不了生活被偶然性所支配的事實(shí),這令人不安。在理性的世界中,可經(jīng)驗(yàn)的事物都是被因果律所決定。“一切在這個(gè)世界中所共同地存有的東西,都是通過一條普遍的因果律,直接或間接地相互依存。由于這種樣式,世界不僅是一個(gè)萬(wàn)有的總體(Allheit),而且是一個(gè)萬(wàn)有的統(tǒng)一體(Alleinheit),即一個(gè)整體(盡管它是無限的)。”
在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》中,昆德拉提到了尼采的輪回觀。輪回為過去、現(xiàn)在和未來建立起了一種存在的鏈條,以因果律作為連接的邏輯。人害怕失去確定性,失去意義,需要一個(gè)因果的鏈條來賦予人的存在和歷史以意義。若是純?nèi)粏尉€的歷史觀,人就難以找到過去與未來的關(guān)聯(lián),也就找不到意義所在。因果的必然性是理性所賦予的,那種堅(jiān)實(shí)的必然性給人以厚重的生活根基。
十八世紀(jì)的理性主義建筑在萊布尼茨的句子上:nihil est sine ratione——沒有任何存在之物是沒有理由的。科學(xué)受到這個(gè)信念的刺激,熱烈地檢視著一切事物的為什么,好讓一切存在之物看起來都是可以解釋的,所以,也是可以計(jì)算的。人,希望自己的生命擁有某種意義,他會(huì)放棄每一個(gè)沒有原因和目的的行為。所有的傳記都是如此寫下的。生命看起來像是一道因、果、成、敗的明亮軌跡,人則是一邊以焦急的目光緊盯著自己行為的因果鏈,一邊繼續(xù)加速向死亡狂奔而去。[米蘭·昆德拉著,尉遲秀譯:《小說的藝術(shù)》]
啟蒙理性的核心是科學(xué)化,科學(xué)成為真理和秩序,人成為科學(xué)理性下的機(jī)器,人類的生活、知識(shí)、情感、審美都可以放置在科學(xué)的眼鏡下進(jìn)行觀察,人文學(xué)科及文學(xué)藝術(shù),也需在科學(xué)理性的框架才能呈現(xiàn)其意義和價(jià)值。理性解釋了世界,同時(shí)也遮蔽了世界的復(fù)雜性。思想的反思要從理性本身開始,所以海德格爾才說:“只有當(dāng)我們終于認(rèn)識(shí)到,被頌揚(yáng)了幾個(gè)世紀(jì)的理性,其實(shí)是思想最頑固的敵人,只有這時(shí),我們才有可能開始思想。”
受到啟蒙理性的影響,人文學(xué)科亦視科學(xué)為榜樣,追求準(zhǔn)確與清晰。哲學(xué)與倫理學(xué)在進(jìn)行判斷,“人總是期望一個(gè)善惡分明的世界,因?yàn)樵谌说纳砩嫌心撤N天生且無法馴服的欲望,讓人在理解之前先行判斷。種種宗教和意識(shí)形態(tài)即建立在此欲望之上。宗教和意識(shí)形態(tài)無法與小說和平共存,除非它們能將小說相對(duì)和模糊曖昧的語(yǔ)言轉(zhuǎn)化為它們必然的教條論述。”
科學(xué)化的理性,簡(jiǎn)化了世界。世界原本是模糊復(fù)雜的,但理性哲學(xué)需要清晰的世界,這種清晰的世界是簡(jiǎn)化的世界,豐富的生活世界被簡(jiǎn)化了。昆德拉說:
簡(jiǎn)化所統(tǒng)領(lǐng)的白蟻大軍長(zhǎng)久以來一直啃噬著人類的生活:即便最偉大的愛情最后也會(huì)被簡(jiǎn)化成一副由淡淡回憶組成的骨架。但是現(xiàn)代社會(huì)的特性像惡魔似的,又強(qiáng)化了這個(gè)詛咒:人的生活被簡(jiǎn)化為它的社會(huì)功能;一個(gè)民族的歷史被簡(jiǎn)化為幾個(gè)事件,而這些事件又被簡(jiǎn)化成一個(gè)戴著有色眼鏡的詮釋;社會(huì)生活被簡(jiǎn)化為政治斗爭(zhēng),政治斗爭(zhēng)又被簡(jiǎn)化為僅僅是地球上兩個(gè)強(qiáng)權(quán)的對(duì)立。人置身于一個(gè)真正的簡(jiǎn)化的漩渦里,在其中,胡塞爾所說的‘生活世界’宿命式地黯淡了,存在墮入了遺忘之中。[《小說的藝術(shù)》]
笛卡爾的哲學(xué)把主體作為核心,近代哲學(xué)是主體哲學(xué)(a philosophy of the subject),以確定性和真理為基礎(chǔ)。
理性傳統(tǒng)的問題不在于它主張理性,而在于它實(shí)際上是一個(gè)“理性優(yōu)先、理性唯一”的傳統(tǒng)。“理性優(yōu)先”表現(xiàn)在“一切對(duì)真理和合法權(quán)威的主張必須提交理性之法庭”,而且這個(gè)理性據(jù)稱有客觀性、普遍性和絕對(duì)真理的權(quán)威。“理性唯一”在于它排斥了人性中的欲望、直覺、無意識(shí)、想象、意志等,視所有這些為“非理性”。[尼采著,黃明嘉譯:《快樂的科學(xué)》]
尼采說:
你們以為對(duì)世界的解釋只有一種是正確的,你們也是以這種解釋指導(dǎo)科學(xué)研究的,而這種解釋僅僅依靠計(jì)數(shù)、計(jì)算、秤重、觀察和觸摸啊,這種方式即使不叫它是思想病態(tài)和愚蠢,那也是太笨拙和天真了。[《快樂的科學(xué)》]
科學(xué)對(duì)于人生問題,根本是無能為力的,科學(xué)的精神化,使得人成為物的奴隸。“所謂‘科學(xué)地’解釋世界實(shí)在愚不可及,荒誕不經(jīng)。本質(zhì)機(jī)械的世界也必然是本質(zhì)荒謬的世界。”科學(xué)所追求的客觀和真實(shí),其實(shí)是一種欺騙,因?yàn)?ldquo;科學(xué)也是以某種信念為基礎(chǔ)的,根本不存在‘沒有假設(shè)’的科學(xué)。”
在《悲劇的誕生》中,尼采的目的便是審視科學(xué):“當(dāng)時(shí)我要抓住的是某種可怕而危險(xiǎn)的東西……它就是科學(xué)本身的問題——科學(xué)第一次被視為成問題的、可疑的東西了。”他希望在藝術(shù)的基礎(chǔ)上反思科學(xué),他把《悲劇的誕生》“立足在藝術(shù)的基礎(chǔ)上——因?yàn)榭茖W(xué)問題不可能在科學(xué)的基礎(chǔ)上被認(rèn)識(shí)。”尼采對(duì)于科學(xué)以及理性主義的反思溯源到希臘哲學(xué),尤其是蘇格拉底那里。他認(rèn)為蘇格拉底就是后來強(qiáng)調(diào)理性、知識(shí)和科學(xué)思想的源頭:“我們整個(gè)現(xiàn)代世界被困在亞歷山大文化的網(wǎng)中,把具備最高知識(shí)能力、為科學(xué)效勞的理論家視為理想,其原型和始祖便是蘇格拉底。”尼采在對(duì)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、悲劇精神和歌劇文化的分析中,深刻地解釋了西方思想在蘇格拉底處的轉(zhuǎn)型,酒神精神的沒落,歌劇文化取代悲劇精神,成為西方文化的一場(chǎng)“悲劇”,這導(dǎo)致了科學(xué)思想的強(qiáng)勢(shì),卻恰恰是對(duì)真理和生存的遮蔽。
悲劇毀滅于道德的蘇格拉底主義、辯證法、理論家的自滿和樂觀嗎?……甚至科學(xué),我們的科學(xué)——是的,全部科學(xué),作為生命的象征來看,究竟意味著什么呢?全部科學(xué)向何處去,更糟的是,從何而來?怎么,科學(xué)精神也許只是對(duì)悲觀主義的一種懼怕和逃避?對(duì)真理的一種巧妙的防衛(wèi)?用道德術(shù)語(yǔ)說,是類似于怯懦和虛偽的東西?用非道德術(shù)語(yǔ)說,是一種機(jī)靈?哦,蘇格拉底,蘇格拉底,莫非這便是你的秘密?[尼采著,周國(guó)平編譯:《悲劇的誕生:尼采美學(xué)文選》(修訂本)]
作為拯救之道,尼采提起了藝術(shù),希望用藝術(shù)拯救人生。他說:“只有作為一種審美現(xiàn)象,人生和世界才顯得是有充足理由的。”“藝術(shù)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來的形而上活動(dòng)。”尼采哲學(xué)的核心在于“強(qiáng)力意志”,對(duì)于強(qiáng)力意志的解釋就是以藝術(shù)為起端的。“如果說對(duì)于尼采來說,在把一切發(fā)生事件(Geschehen)都解釋為強(qiáng)力意志這樣一項(xiàng)任務(wù)的范圍內(nèi),藝術(shù)具有一種突出的地位,那么,恰恰就在這里,關(guān)于真理的問題也必然起著一種首當(dāng)其沖的重要作用。”藝術(shù)因?yàn)殛P(guān)涉人的存在而關(guān)涉真理,從而關(guān)涉人的生活本身,從而,在理性主義和科學(xué)主義的壓抑下,藝術(shù)有了拯救的力量:“藝術(shù),無非是藝術(shù)。它是生命的偉大可能性,是生命的偉大誘惑者,是生命的偉大興奮劑……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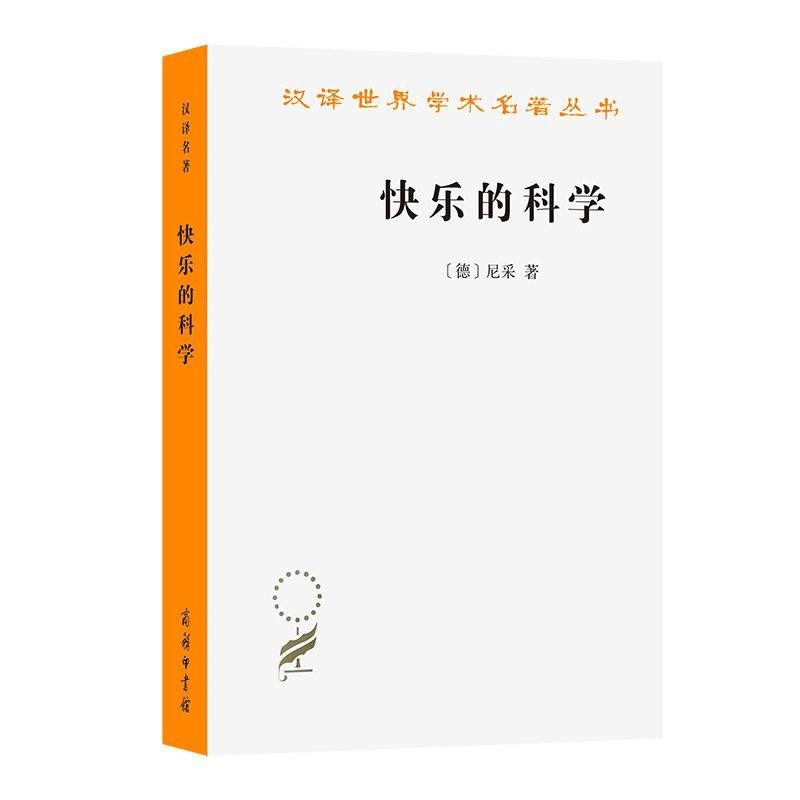
生活是陷阱,人是被拋進(jìn)這個(gè)世界的。理性在言說著生活的合理性,但卻掩蓋不了生活的非理性與荒謬。昆德拉在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》中說:“小說不是作者的告白,而是在這已然成為陷阱的世界里探索人類的生活。”何以說世界是陷阱呢?昆德拉在另一處說:“生活是一個(gè)陷阱,關(guān)于這個(gè),人們從來就知道:我們不曾提出來要求就被生了下來,被關(guān)在一個(gè)我們不曾選擇并且注定要死去的軀體里。”
現(xiàn)代的心理分析(psychoanalysis)對(duì)理性主體進(jìn)行了解構(gòu),在心理分析看來,人是受非理性支配的存在。“弗洛伊德說,他有兩個(gè)基本的發(fā)現(xiàn)‘足以觸怒全人類’。一是發(fā)現(xiàn)有意識(shí)的思維活動(dòng)底部還有一個(gè)廣闊得多的‘無意識(shí)’存在;二是發(fā)現(xiàn)‘性本能’是人的精神活動(dòng)的核心。”
在理性的思考中,在因果邏輯下,人類是嚴(yán)肅的,一本正經(jīng),但不知生活的趣味。在昆德拉看來,拉伯雷有一個(gè)被人忽視的創(chuàng)造,那就是發(fā)明了一個(gè)新詞“扼結(jié)樂思忒”(agélaste),這一源自希臘語(yǔ)的詞,意為“不笑的人,沒有幽默感的人”。這種人不懂文學(xué)的智慧,生活的樂趣,令人害怕。這些人“從來不曾聽到上帝的笑聲,他們相信真理是清晰的,他們相信所有人的想法都應(yīng)該相同,他們相信自己和心里所想的自己一模一樣。然而人之所以成為個(gè)人,恰恰是因?yàn)樗チ藢?duì)真理的確信以及其他人的一致共識(shí)。小說,是屬于個(gè)人的想象天堂。在這片領(lǐng)土上,沒有人是真理的占有者,安娜不是,卡列寧不是,在這里,所有人都有權(quán)力被人理解,安娜有,卡列寧也有。”小說有著與哲學(xué)不同的智慧和邏輯,“小說的智慧和哲學(xué)的智慧是不同的。小說并非誕生于理論的精神,而是誕生于幽默的精神。”
啟蒙現(xiàn)代性讓人類陷入到“存在的遺忘”之境遇之中,是文學(xué)承擔(dān)了尋找存在的責(zé)任。“一門偉大的歐洲藝術(shù)因?yàn)槿f(wàn)提斯而成形,而這藝術(shù),正是對(duì)被遺忘的存在進(jìn)行的探索。”在米蘭·昆德拉看來,塞萬(wàn)提斯與笛卡爾同為現(xiàn)代的奠基者。塞萬(wàn)提斯將世界理解為一團(tuán)模糊曖昧、相互矛盾的存在,在乎的是“關(guān)于不確定事物的智慧”(sagesse de l’incertitude),追求相對(duì)真理。

王宏超在工作坊上發(fā)言
人的價(jià)值觀、欲望、情感、審美,是難以被啟蒙理性進(jìn)行簡(jiǎn)化的。由此,有了美學(xué)的現(xiàn)代性(aesthetic modernity)來對(duì)啟蒙現(xiàn)代性加以反思。“美學(xué)判斷除了非功利的特質(zhì),還將理性、想象、直觀、欲念融為一體,形成更為成熟的判斷,因而不同于以理性為唯一特征的體系現(xiàn)代性。沒有20世紀(jì)之前現(xiàn)代經(jīng)典文學(xué)的美學(xué)積累,我們未必能明辨現(xiàn)代體系的問題所在,也就沒有直逼要害的眼力。”
而文學(xué)的使命是什么?是去體現(xiàn)哲學(xué)思考,成為歷史的片段嗎?若是這樣,那文學(xué)僅是一種傳聲筒而已。昆德拉傳述赫爾曼·布洛赫的看法說:“發(fā)現(xiàn)那些唯有小說才能發(fā)現(xiàn)的事,這是小說唯一的存在理由。一部小說如果沒有發(fā)現(xiàn)一件至今不為人知的事物,是不道德的。”奧威爾的小說雖然優(yōu)秀,但他的作品講述的東西和一篇論文與評(píng)論中所言的內(nèi)容是一致的,發(fā)現(xiàn)“唯有小說才能發(fā)現(xiàn)的事”,才是小說的使命所在。
小說的智慧與哲學(xué)的智慧不同,“小說的精神是復(fù)雜的精神。每一部小說都對(duì)讀者說:‘事情比你想象的復(fù)雜。’這是小說的永恒真理,但是在簡(jiǎn)單快速響應(yīng)的喧嘩之中,這樣的真理越來越少讓人聽見了,喧嘩之聲先于問題而行,并且拒斥了問題。對(duì)我們時(shí)代的精神來說,要么是安娜有理,要么是卡列寧有理,而塞萬(wàn)提斯卻向我們?cè)V說著知之不易,告訴我們真理是無從掌握的,可他老邁的智慧卻看似笨重累贅又無用。”
小說作為這個(gè)世界的模型,奠基于人類事物的相對(duì)性與模糊曖昧,小說和極權(quán)的世界是互不相容的……這種不兼容,是本體論的(ontologique)。也就是說:根植于唯一真理的世界與模糊曖昧又相對(duì)的小說世界,是用全然不同的材料捏出來的。極權(quán)的真理排除相對(duì)性,排除懷疑,排除質(zhì)疑,這真理與我稱之為小說精神的東西也就永遠(yuǎn)無法和平共處。[《小說的藝術(shù)》]
黑格爾用理性來解釋戰(zhàn)爭(zhēng),“在荷馬的作品里,在托爾斯泰的作品里,戰(zhàn)爭(zhēng)擁有十足清晰可辨的意義:人們?yōu)榱嗣利惖暮惢驗(yàn)榱硕砹_斯而戰(zhàn)。帥客和他的同袍走向前線,卻不知為何而戰(zhàn),而更令人驚訝的是,他們對(duì)此沒有興趣。”海德格爾把戰(zhàn)爭(zhēng)看作是“追求意志的意志”(volonté de volonté)。“為什么昨天的德國(guó)、今天的俄國(guó)想要統(tǒng)治世界?為了變得更富有?更幸福?不。這種力量的侵略性對(duì)此完全沒有興趣;沒有動(dòng)機(jī);它只想追求它的意志;它就是純粹的非理性。”

同哲學(xué)一樣,“過去的小說家試圖在奇異而混沌的生活材料里,抽出一條清晰、合理的線索;在這些小說家的透視法里頭,可以合理解釋的動(dòng)機(jī)產(chǎn)生了行為,行為又引起了另一個(gè)行為。冒險(xiǎn)則是一連串的行為,行為之間的因果關(guān)系清清楚楚。”因果是簡(jiǎn)化世界的方式,真實(shí)的生活世界中,許多事情是沒有因果關(guān)系的。但現(xiàn)代的文學(xué)還原了世界的非因果狀態(tài),“在那兒,因果之間的橋梁被摧毀,思想在無所事事的甜美自由里游蕩。存在的詩(shī)意……它處在離題之中。它在無法計(jì)算的事物之中。它在因果關(guān)系的另一邊。它sine ratione——是沒有理由的。它在萊布尼茨的句子的另一邊。”
在昆德拉看來,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最偉大的功績(jī)之一,就是“闡明了人類行為的無因果性、無法預(yù)知的甚至神秘的一面。”因果關(guān)系可以解釋維特的自殺,但卻無法解釋安娜的自殺。
安娜去火車站迎接情人弗龍斯基,她乘坐火車到達(dá)了車站,被生活與情感折磨的安娜,總算擺脫了火車上遇到的一對(duì)虛偽聒噪的夫婦:
她在站臺(tái)上停下來,竭力回想她干嗎上這兒來,打算來干什么。她覺得以前能夠辦到的事,如今卻變得如此難以揣摩,特別在這群吵鬧得不讓她安寧的、胡天胡地的人中間。[列夫·托爾斯泰著,高惠群、石國(guó)生譯: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,下同。]
但安娜只是等到了弗龍斯基草草的一封信,他還沒回來。安娜的內(nèi)心又遭受了一次羞辱性的致命一擊。
“不,我不會(huì)再讓你折磨我了”,她暗自尋思,既不是嚇唬車夫,也不是嚇唬自己,而是嚇唬那個(gè)使她受盡折磨的人。
她走在站臺(tái)上,卻不知道走向何處,感覺周圍的人在議論她,“一些年輕人不讓她安寧。”
“哦,天哪,我要到哪里去呀?”她這么想,一邊沿站臺(tái)越走越遠(yuǎn)。
安娜的心緒很亂,她何止不知道該走向哪里,她也不知道人生該走向何方。她像浮萍,難以把持命運(yùn)的航線。正在這個(gè)極度迷茫的時(shí)刻:
驀地,她想起她與弗龍斯基第一次相會(huì)那天被火車碾死的那個(gè)人,頓時(shí)明白,她該怎么做了。她邁著輕捷的腳步從水塔那里走下臺(tái)階,來到鐵軌邊,在行駛的列車的跟前站住了。
安娜的決定并非一系列理性思考的結(jié)果,盡管有迷茫、悲傷、屈辱、絕望,但這些現(xiàn)實(shí)中的事件似乎也不必然引她走上鐵軌。昆德拉說:“她撲到火車底下,并非事先做了決定。應(yīng)該說是這個(gè)決定抓住了安娜。”
安娜似乎也有理性的思考,“我要懲罰他,我要擺脫所有的人,要擺脫自己。”為懲罰別人而自殺,這是一個(gè)自殺的理由,但很難說是個(gè)合乎理性的理由。人很多時(shí)候似乎就如此受到非理性的情緒左右,所做出的決定比理性更堅(jiān)定,或許也更合乎自我之期待。安娜在那一刻時(shí)歸于了內(nèi)心的平靜:
這時(shí)候,類似游泳入水前的那種感覺攫住了她的內(nèi)心,于是她畫了十字架。畫十字的習(xí)以為常的動(dòng)作,在她心里喚起了一系列少女時(shí)代和童年時(shí)代的回憶,這時(shí)籠罩著她周圍一切的那片黑暗突然劃破了,她眼前剎那間又呈現(xiàn)出昔日生活全部美好、歡樂的光輝景象。
昆德拉的小說不再講述“光榮、榮譽(yù)、勇氣或神圣”(海明威在《永別了,武器》中說:“我總是為神圣、光榮、犧牲這些字眼的濫用感到難堪。”),他選擇講述輕、快、精確、形象和繁復(fù),講述孤獨(dú)、無聊和虛無,他選擇跟隨了塞萬(wàn)提斯、塞繆爾·理查森、福樓拜、托爾斯泰、馬塞爾·普魯斯特、詹姆斯·喬伊斯……在宗教、哲學(xué)、科學(xué)不能庇護(hù)人類之后,文學(xué)成了拯救人類精神的最后歸宿。
文學(xué),在擺脫了理性的鉗制之后,不正是被用來拯救被遺忘的生活的原初意義嗎?
